弼猷先生诗语出自然,不拘绳墨,然佳句连篇,譬句屡见,无不耐人吟味,启人深思,颇得魏晋风骨。其早年“英文诗词字字精练,扬华夏之心声,文则笔墨生动,传祖国之文化,深受彼邦评坛重视……现先生中英诗文将合集问世,二者交相辉映,堪称双璧。——冯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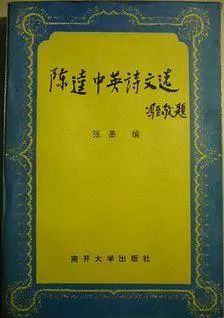
吴宓曾称陈逵为“中国今时之雪莱”,并说“世之知雪莱,爱雪莱者,当亦知、爱陈逵也”。还说陈先生的诗“境真、情真、理真,可谓真诗”。
1947年,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上海工人、市民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市政当局派军警弹压,每天都有人被逮捕、暗杀。这天,在复旦大学一个教室里,一个身穿长袍的中年教授走下讲台,开始抨击起时政,浓眉下的一双怒目闪着精光。忽然,他用英文高声吟诵起英国诗人雪莱的名篇《西风诵》: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学生们激动地齐声复诵,声震校园。这位教授便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陈逵先生。
吴宓曾称陈逵为“中国今时之雪莱”,并说“世之知雪莱,爱雪莱者,当亦知、爱陈逵也”。还说陈先生的诗“境真、情真、理真,可谓真诗”。
世上有狂人也有儿童/狂人是我的老师/儿童是我的朋友/我愿与儿童一起跟随狂人/走向那光明的土地。
这是1925年,陈逵写的《狂人和儿童》。表达了他对光明的追求:
我像一只野鸭/生活在辽阔的海上,或海一样的大湖上/过分的舒适,对我来说却像个鸟笼/像一桶冷水倒在燃烧的火上。
这是1929年,陈逵写的《我像一只野鸭》,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
进入美国文学殿堂的中国青年
陈逵,字弼猷,1902年7月出生在湖南株州攸县凤岭乡(今柏树下乡)樟井村。他5岁进入私塾,学了《诗经》、《论语》、《孟子》、《左传》、《史记》、《战国策》,以及唐诗、宋词。塾师是他母亲的叔父,这位老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非常重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
1928年,陈逵曾用英文写了一篇自传,发表在英文文学刊物《日晷》上,文中对这位叔外祖父有着生动的描述:他是退了休的地方行政长官,为政清廉,学问又好。我为父母能为我聘请到这样一位先生为启蒙老师而荣幸。我的父母很郑重地选择了文曲星显露的那一天作为我举行从师庆典的日子。晚上,我叔外祖父到达我家,用白色的小陶瓷杯和我父亲喝老酒。他们谈论的主要问题是读书和成才。酒后吃饭,新添一碗豆腐汤。叔外祖父说:“豆腐汤表现了乡村的淳朴。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在他的书房里张贴了这样一首小诗:客人来吃饭,豆腐加盐蛋。勿忘君子交,请忘此便餐。博览群书对一个学者来说是第二重要的,品行修养才是第一位的。”
陈逵上小学时,辛亥革命爆发。他曾写道:“革命的势头很大。革命已深入人心。191 1年,确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结束了帝制……”他还描写了当时剪辫子的情况:一个来自有革命政府的城市的官员到了我们村子,他把两幅布告贴在我们村豆腐店的土墙上,然后开始讲演。演讲毕,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大声喊叫:“谁做第一个?”大家都互相看着,希望别人做第一个,似乎他们都认为聪明的人不应首当其冲。官员摇摇头说:“有些人像笼中鸟,他们不在乎自由,即使门是打开的,他们也不会跑出去。”自那天后,那些仍然留有辫子的人便把辫子盘在头顶。这对双方都是一个愉快的结果。这样,一方面可以认为对方不过是守旧派;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担心清朝皇帝再回来。
少年陈逵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他认为这种中间结果对双方都不光彩。对老百姓来说,是在光明来到时的麻木不仁;对革命政府来说,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但他那时毕竟还是个只有九岁的少年,无能为力。但他心中已燃起了追求光明的火。他说:“我既高兴又自豪。因为我不像其他人,我从来没有留过辫子。我不愿做,也没有当过奴隶。”
1915年,陈逵进入了长沙明德中学学习。这所中学是民初著名教育家胡元倓于1913年创办的。
1920年,陈逵赴美国勤工俭学,先后在耐不拉斯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研习文学和哲学。1925年,他即开始在美国《世纪》、《书人》等刊物上发表英文诗。1926年,在耐不拉斯大学毕业典礼上,他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
1927年至1928年,陈逵的英文诗创作达到高潮。曾五次在美国最有影响的《日晷》杂志上发表作品。与此同时,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了美国的《诗刊》上。该刊每期限发二十五首诗,审稿非常严格,而他几乎是每稿必发,这让他成了美国当时最活跃的东方诗人。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陈逵得知消息后彻夜难眠,他满怀悲愤地写了短篇小说《耻辱》,在纽约《民族周刊》上发表,引起了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士的义愤和关注,收到读者来信百余封。1905年创刊的英文期刊《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向以报道、分析时事政治为己任,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为祖国的命运担忧。顾维钧、王景春、郭秉文、宋子文、蒋廷黻、梅汝撤等人都曾担任过该报的主编。1927年8月,陈逵也被选为了《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
那时,在美国密西西比州,黑人和白人的儿童是分校读书的,1927年10月,该州教育委员会决议:华裔儿童只能进黑人学校。《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将这一消息原封不动地登载在第一页上,只加个了标题《美国之愚昧的暴露》,另外还刊登了乙未生的两张讽刺帝国主义的名为《残害殖民地人民》和《文明人的假面揭破》的漫画。
这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首先是美国在华商人的代言人、美国中国学会代理书记辛普森于12月来信,认为《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对美国采取了不友好的方针;接着美孚石油公司也来信,说若不改变方针,他们今后将不再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登广告。陈逵将辛普森的信刊登在下一期报上,并给出了一封答复信,对他的观点一一给予驳斥。这引起了美方一些人士更大的不满和指责,同时也引起以杜威为首的一批美国教授的注意,他们联名成立了“争取中国自由防卫委员会”,为在美华人争取平等权利。远在柏林的史沫特莱女士也写信赞扬说该报的“编辑方针是空前的”。
1982年,美国贝宁顿大学文学系主任、哈佛博士菲比•赵女士应邀来华讲学,当得知陈逵仍健在时,还在课堂上高兴地对同学们说:“你们应当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旱在20年代末,就和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大诗人一样,在美国一流的期刊《日晷》上发表英文诗了。”
他是最早结识史沫特莱的中国学人
1928年秋,陈逵回到祖国,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十余所大学任教,并创办了南开、湖南大学两校的外文系。
在长夜待旦的旧中国,陈逵使不少学生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后来担任了上海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总编辑的陈怀白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传写道:陈逵在教《文学入门》时,常联系课文讲解社会问题,使怀白懂得:人应该为争取自由而勇敢地反抗……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作者在这本书上签了名,送给陈老师。陈转借怀白阅读,怀白深受教育,开始懂得妇女要求得解放,须和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必须参加革命斗争。怀白写了读后感,由陈老师批改后寄给史沫特菜。不久接到史的回信,大意是:祝贺那个写读后感的姑娘。她写得很好。但也从中看到中国的姑娘们在革命中总是被动地躲在后面,这是不能令人鼓舞的。史的批评,使怀白震惊,开始思索道路该怎么走……1935年,史沫特菜的新著《中国红军在前进》出版,同样送陈逵一本,陈照例借给怀白看。从新作中,怀白知道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业是如此壮丽!
后来,在抗战的炮火迫近校门时,陈怀白终于下了决心,放弃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选择了革命道路,参加了新四军。
陈逵和史沫特莱的交往早在1928年2月即已开始,这是中国人和史沫特莱的最早交往。陈逵和史沫特莱的友谊使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52年春,遵照史沫特莱的遗愿,她的骨灰的一半自伦敦运至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逵写了一阕《减字木兰花•敬挽史沫特莱女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陈逵在教学中常借题发挥,联系现实揭露旧中国的黑暗。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有一次他选了一首题为《林肯半夜踯躅徘徊》的英文诗给学生学习。诗的大意是,美国总统林肯生前宣扬自由平等,号召人们为之战斗、牺牲,但在他去世后多年,美国并没有真正自由平等,因此他在黄泉下不能安息,半夜里阴魂起来踯躅徘徊。在讲完这首诗后,陈逵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每人写一首题为《孙中山先生半夜踯躅徘徊》的英文诗。很明显,布置这个作业的目的是启发学生揭露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而实际上是叛徒的那些人的反动本质,揭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说明三民主义并没有实现。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人心惶惶,不少人逃往香港、台湾,陈逵利用英语课堂向学生宣传“中国势在必变”、“留为上策”等道理,这对一些中间状态的同学起了影响。不仅如此,陈逵还说服一些友人不要跟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陈衡哲是我国第一位女教授,自1929年在北平与陈逵相识后,时有往来。1949年春,陈衡哲的丈夫任叔永已飞到香港,等候妻子抵港后,一块儿赴台湾,陈衡哲也已机票在手,但经与陈逵两次交谈后,最后决定留下。1950年,任叔永也从香港返回了大陆。著名学者沈尹默先生也是因为陈逵的说服留下来的。
陈逵自己则更是拒绝了去台湾的诱惑,积极参加进步组织“大教联”的一些活动。上海刚解放,组织上便聘请陈逵和一些进步人士到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工作。陈逵欣然应命。当时上海《大公报》作过题为《陈逵教授等八人参军北上》的报道。
陈逵从选材到教课,任劳任怨,“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一次,他和大家一样背着木椅整队到大操场听报告,他的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恰好坐在他旁边,关切地问他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陈笑答“能行”。叙谈中,陈逵有句话使这位学生印象深刻,那就是“你看,国家充满了希望,我也充满了希望”。一个老知识分子热爱新中国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英译毛泽东诗词第一人
为了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陈逵于1924年就开始了汉诗的英译工作,翻译了不少白居易、元稹、王维等唐代诗人的诗篇,还有《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20世纪50年代,陈逵但任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杂志的顾问和编委,也用英文写过介绍陶渊明、白居易的文章。
陈逵的另一项工作是与王培德先生一起合译英国古典名著――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
1951年,陈逵被聘为《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
1957年,在印度出版的《亚非评论》发表了陈逵译成英文的《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长征》、《西江月•井冈山》等八首毛泽东诗词。据目前掌握的资料,陈逵是第一个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的人。
此时,陈逵的英文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同时,因为植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他的中文诗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使得他的中西诗文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正如谭佛雏教授在《陈逵师旧体诗整理后记》中所说:先生精研西方文学,尤其是诗歌。而他于传统诗歌,也同样深深喜爱与熟谙。故他的旧体诗往往呈现出一种中西融合的情味。如《陈逵中英诗文选》开头一首《人间》(1931):“人间有樊笼,囚我性灵鸟。白昼昏睡去,哀鸣暮达晓。”我想,恢张自我“性灵”,实为先生中西诗作的“第一义”。另如《忍耐》(1939):“忍耐与希望,譬如鸳与鸯。合则长悦乐,分则各矢残。”此是五绝形式,实已注入新词汇与内容。写法也很新颖,构成了一种颇富理趣的妙语。然先生仍极重纯粹的传统诗的格律。如《寄冯至兄》(1943):“无才催短命,养气度长冬,岂羡乘肥马,不如学老农。折腰难得饱,仗剑欲何从。踽踽颇知乐,栖栖敢自封。”对仗、平仄,工稳妥帖,置之古人诗集中,亦复难以辨别。
1990年1月,陈逵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八岁。
1995年,为纪念陈逵逝世五周年,南开大学出版了由陈逵先生的夫人张墨及其子女整理的《陈逵中英诗文选》。老诗人冯至撰写书名,并写了序。冯至先生写道:弼猷先生诗语出自然,不拘绳墨,然佳句连篇,譬句屡见,无不耐人吟味,启人深思,颇得魏晋风骨。其早年“英文诗词字字精练,扬华夏之心声,文则笔墨生动,传祖国之文化,深受彼邦评坛重视……现先生中英诗文将合集问世,二者交相辉映,堪称双璧”。
陈逵骨灰的三分之一撒在了太平洋里,三分之一撒在了湖南的湘江中,三分之一撒在了攸县柏市镇的罗浮江。这位“中国的雪莱”、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大家,便这样默默地回归了他所喜爱的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