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译作是出版社的主攻方向之一,过去恐怕从来没有过这样持久的大规模翻译出版运动。做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有不少是文笔精湛的外文专家,有些甚至是翻译家。而现在从事历史、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翻译的译者当中,资深的学科专家并不多,敷衍了事赶活的普通学者不少,有的甚至还是在校学生。当下翻译出版的质量令人担忧,粗糙的文字和严重的错误是很平常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除了外文院系,其他学科都不太承认翻译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听说有的外文院系最近也在更有决心地转向研究和强调论文发表,翻译也将不再被看作是学术成果。
把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究竟算不算是研究工作,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进行调查分析的问题。把经典的文史名著和社会科学著作翻译成信、达、雅的中文是一种高难度的再创作,这与亲缘关系密切的印欧语系各语言间的互译可能情况不同。如果我们不鼓励学者去认真从事翻译工作,而任由大量粗糙译作在市场上流行,目前这场规模空前的翻译运动的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大家可能都有经验,现在看不懂的译作实在是太多了。高峰枫教授甚至写过《西塞罗的愤怒》,感慨译者对经典作品的糟蹋。
好的翻译本身就是创作,甚至本身就是艺术品。

多年前当学生的时候,为学英文,读过很多毛姆的短篇小说,被其中的一个故事深深打动:一个35岁的英国银行职员到一个地中海小岛度假,迷恋上了那里的美好生活,于是下决心辞去工作。他放弃了工作满30年拿养老金的机会,用自己的所有财产买了一笔够他生活25年的年金,计划在岛上悠闲生活到60岁,之后就死而无憾了。我后来收藏有企鹅版的4卷本毛姆短篇全集,想再看一遍这个故事,却没有耐心一篇篇去寻找。实际上毛姆故事的背景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普里岛,而我不仅忘记了小说的题目,也把故事的地点误记成了希腊。所以后来在访问希腊的时候,我面对梦幻一样的艳蓝天空、深蓝的海浪和油漆成白色的一栋栋小房子,又想起这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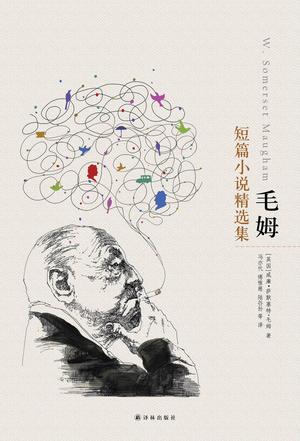
前几天买到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本来买这本书是因为看到各篇译者都是名家,并没有打算逐篇去重读,但是看到陆谷孙先生为他自己翻译的那篇写了详细的译后记,于是就去翻阅,发现这篇就是多年在我脑中萦回的那个故事《吞食魔果的人》。
陆先生这篇译后记《“食莲”还是“吞枣”》,是针对故事标题的翻译写的。因为该标题里面提到的“魔果”通常是指中文所说的“睡莲”,而由故事情节看,毛姆所指的是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即“落拓枣”。在希腊神话里,这是食用后会产生幻觉的忘忧花果,陆先生因此译故事篇名为《吞食魔果的人》,而不取“食莲人”这个看似更加优雅的译法。后者显然很难与故事的内容对应。董桥先生回应陆先生的文章干脆说,“毛姆这个短篇的题目害苦中国几代读书人难进难退”。
如果经典的文学和社会科学著述的翻译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应该被视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其他外文作品的翻译是否就可以轻视呢?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有不少在国内被翻译出版,这些作品的翻译除了需要非常熟悉英文,还需要对美国文化和日常生活有海量的知识。
像这些翻译,如果不被看作是学术研究,起码应该有丰厚的报酬,以便译者能够从容和专心致志地工作。现在我们经常提起傅雷先生,却经常忘却傅先生的生活一直在很大程度依赖其翻译的稿费。傅先生的翻译是精心推敲的,他甚至是高产的,但是和当下一般的译者相比较,他肯定是动作很慢的。

即便是流行小说和通俗艺术作品的翻译,我们也不宜贬低和看轻。我除了收藏毛姆的小说,也是鲍勃·迪伦的粉丝,后者刚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估计他的歌词会被大量翻译出版。那么,翻译这类通俗作品算不算是一种文学再创作?可不可以算作外文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
有一位研究外国文学的朋友翻译出版了大量诗歌,最近他和我说,花费精力时间翻译会影响写论文,想不好是否继续这样的工作。我是他的忠实读者,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和鼓励他。
难道要劝他吃一枚落拓枣吗?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彭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