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半球介绍中国文化不易,而介绍中国戏曲更是不易。水墨画可以尽在不言中,戏曲却不但要译,还要讲解,从历史、人物直到身段、水袖,一句句唱词、一个个眼神,都得用生动、贴切的外语讲出其间意味。
这中间,向西方观众介绍昆曲更是难上加难。
昆曲唱词清雅高深,曲律规范严谨,问世六百多年来,她既是贵族文士专享的审美,又经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而成。
而这当中,最值得介绍、也最不易介绍的,便是昆曲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牡丹亭》。
汤显祖的《牡丹亭》原作本有五十五出,近代昆剧将其提炼成游园、惊梦、寻梦、离魂、冥判、拾画、叫画、幽媾、冥誓、回生、婚走等十二出,但今日即便是对国人讲《牡丹亭》,也须深知其版本背景和百年提炼过程才能道出其底蕴之美。
昆曲这种不效皮黄的清高,不媚市井的风骨,既令她曲高和寡,也恪守了独有的典雅。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朝飞暮倦,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如何让今日观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感受到这般优美旖旎?2004年5月,深爱昆曲的白先勇在台北推出了《青春版牡丹亭》,演出大获成功,随后移师大陆,立即在国内也掀起昆曲热潮。

青春版《牡丹亭》
接着,白先勇又将她带到了美国,决意向英语圈观众传达昆曲之美。
白先勇非常清楚他所面临的困难。要让《牡丹亭》在美国打响,需要一位同时精通英语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与戏曲,并且对昆曲的演出非常熟悉的人来做中介。有一个人,是做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
这个人,就是他的老朋友汪班。
“汪班长年在美国向美国学生讲授中国诗词书画,他本人不仅娴熟中国诗词传统,而且英文根基扎实,中诗英译,十分在行。加以汪班又曾经票过戏,工小生、小丑,舞台上的戏剧效果,他当然认识深刻,因此他的昆剧选译,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处处透露巧思,很容易引起观众和读者的共鸣。”(白先勇序《悲欢集》:“弘扬昆曲于海外”)
在剧组赴美演出的前几个月,白先勇便专门从纽约将汪班请到加大伯克利分校,做了一系列的昆曲讲座。在每场演出前还有半小时的导读。白先勇说:“汪班学养丰富,对昆曲以及中国传统戏曲有独到见解,而且他口才极佳,言辞生动,极受美国观众欢迎。青春版《牡丹亭》在伯克利首演成功,汪班先生的昆曲讲座功不可没。”
的确,二OO六年九至十月间,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到美国西岸巡回演出一个月,演出十二场,场场满座,受到美国观众空前的热烈欢迎。论者甚至认为这是继梅兰芳来美巡演后,中国古典戏曲对美国文化界产生的最大一次冲击。

汪班与白先勇
汪班祖籍江苏灌云,伯父是同盟会员,父亲怀着报国之志,十几岁就加入了国民党。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公派赴法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都相熟。回国后便进入国民政府工作。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是抗战时期被派往第三战区(主要包括江、浙、闽、赣、徽地区,司令长官为顾祝同),负责战时学校的工作,包括为逃难的孩子们办的流亡学校。战时学校大多散布在日军难以抵达的闽东偏远山区,条件极为艰苦,然而在战火纷飞中,就是它们给流离失所的孩子们提供了一张课桌、一个安身之所,为国家保育下“读书的种子”。
汪班1939年生于战时首都重庆,1949年随家人去往台湾。1961年从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毕业后,他远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专业。密大是新闻学重镇,然而汪班很快发现新闻并非自己所喜。同时,密苏里的空旷寂寥,使喜欢人文教化的汪班难以忍受。于是他转学到位于新泽西的西东大学,继续学习英语文学。毕业之后,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教授中国语文与中英翻译,并以英语讲授中国文学课程。汪班独创的教学方式和生动细腻的讲授,非常受学生欢迎;他的英文水平,以及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独到见解,令同在哥大任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家夏志清激赏,夏志清曾开玩笑地说汪班和自己是当代两大“苏州才子”——夏志清是吴县人,汪班母亲来自苏州望族袁氏。
汪班的英语是“童子功”:抗战胜利后,汪家搬回上海,他入读中西小学,这是所中英文双语教学的教会学校;不过因为身体弱,加上时局纷乱,他并没有好好上学。但他家里还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他母亲的好朋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一直住在汪家。汪家的孩子就跟着这位“嬢嬢”学英文,到十几岁时,汪班已经能整出地背诵莎士比亚的剧作。
汪班对戏曲、音乐的喜爱同样始自少年时代。他从小就喜欢唱歌,而且嗓子极好,跟着爱唱歌的大姐学会了很多中英文歌曲。但回上海不久他就得了伤寒,这在当时是极凶险的传染病,汪班足足有六个月被隔离在病房,每天除了开诊所的姨父父子会来看他,陪伴他的只有一台收音机,听来听去,除了流行歌曲就是戏曲——小孩子对新闻之类的节目自然没兴趣。他就这样爱上了京剧、昆曲。这倒与白先勇颇类似:白先勇也是在少年时代患上肺结核,不得不隔离治疗,百无聊赖中,通过收音机爱上了京昆。
不过汪班与白先勇相识是在大学时代:他有一位大学同级校友是白先勇的弟弟。汪班读的外文系,与这位读理工的校友没有亲近起来,却与白先勇因为共同的爱好很快成为至交。
汪班第一次翻译昆曲是在1980年,观赏了上海昆曲团的纽约演出之后,他应纽约海外昆曲社之邀,开始为演出的昆曲作英文翻译。他在《悲欢集》的自序中说:
记得第一部“思凡/下山”,是乐而不淫、谐趣横生的名剧,词句俗中带雅,不但饶富诗意,也有极逗人的通俗性,要将它移植到英语的土壤里,对我是件特别新鲜的事儿,极具挑战性,因而觉得又刺激又兴奋,用心推敲,仔细地将它们译成了押有音韵的英文。
由此开始,在之后的十八年时间里,汪班陆续译出四十多出昆曲折子戏,以及两出全本昆剧:《十五贯》和《春草闯堂》,配合了几十场昆曲演出。
接着,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林肯中心、华盛顿国家艺术馆、英国BBC等纷纷邀请他以英语作昆曲专题讲座。他也担任了纽约昆曲社顾问兼首席翻译,并与纽约昆曲社合办专场演出,敦请中国昆曲大师如张继青、蔡正仁等赴美东表演。纽约时报音乐评论家Jamesc Ostreich非常欣赏汪班对昆曲的讲解,称其"气象万千"(1998.7)、"引人入胜"(1998.8),"多彩多姿"(2003.9)。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汪班先生翻译的《牡丹亭》那段千古绝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原文见前文):
These multiflorate splendors, here in magnidicent blosom,
Seem forlorn amidst the raveged foutains and walls!
Oh, it is in vain this fleeting moment of beauty has come:
For yhe enjoyment of spring belongs in other halls.
Oh, clouds, floating hither and yon, day and night:
How the emrald-green halls are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rosy lights!
And how the fine mist, borne on a teasing breeze,
Shrouds the painted boats in distance, as if themselves on clouds!
Alas! Spring,none of your riotous beauty Is for those in locked mansions to see!
由于汪班所作昆曲翻译和推广,1988年以来,纽约昆曲社先后获得纽约文化艺术局以及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赞同与资助。
2003年,纽约市政府为汪班颁发“对文化有特殊贡献最杰出公民奖”。
2009年,汪班翻译的中英双语昆曲选《悲欢集》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
2018年,汪班又出版了中国古诗词英译《撷芳集》。
汪班说,中国古典翻译做不好,对不起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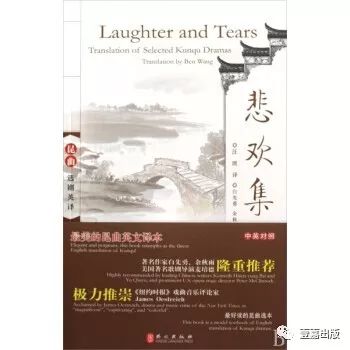
《悲欢集》,外文出版社2009年版

《撷芳集》,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
还值得一提的是,汪班先生的姐姐汪珏,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翻译家、作家、古籍善本专家。她的翻译工作是从白先勇的作品开始的。那是1970年代,她担任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东方藏书部主任,常有人来借白先勇的书,希望有德语版,当然,那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鲜有德语译本,他们只能失望而归。汪珏为之抱憾不已,她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不能来做这个翻译工作呢?她与好友、汉学家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提议二人合作,共同翻译。两人一拍即合,于是,白先勇、沈从文、张爱玲、莫言、杨牧等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不断地经由她们的手译为德文。她们(与包惠夫合作)翻译的张爱玲作品集以《色·戒》为题在德国出版后,立刻获得《时代周报》、《镜报》、《法兰克福日报》等重要报刊好评,汉学家史迪曼(Tilman Spengler)发表文章说“张爱玲几乎是不能翻译的,但是洪素珊、汪珏与包惠夫做到了,而且值得喝采!”详见《翻译张爱玲》(摘自汪珏《流光徘徊》,壹嘉出版2017年版)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壹嘉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