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些论坛讨论钱锺书的翻译水平时,有人以“御用翻译”来称呼1949年后的钱锺书,言语中不无讥讽。一位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闻名于世的学者、作家,为何被冠以“御用翻译”的头衔呢?这还得从他1949年后参与的一系列翻译工作说起。
翻译《毛泽东选集》
1949年8月26日,钱锺书从上海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清华园。他在清华很受重视,工资比余冠英、吴组缃等都高。但他在清华只工作了一年,1950年仲夏,清华同学乔冠华来找他翻译《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把他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工作。据说当初乔冠华是找费孝通参加翻译的,而费表示,自己的英译水平恐不足胜任,于是推荐钱锺书担当此事。消息传出,一位住在城里的老相识,清华校庆时过门不入,现在却马上雇了人力车专程来祝贺。钱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版)
钱锺书并非中共党员,为何会被调去担任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呢?除了自身专业技术水平高,乔冠华的举荐自然是关键。对钱钟书一直比较关心的另一位清华同学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同时也是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员,他的作用也不能忽略。此外,正如何其芳所言,中央对钱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党对他是了解的,信任的。还有一种说法,选择钱钟书参与翻译《毛选》,是因为他出身牛津,受过严格的牛津语音训练,文字风格称得上是“noble”(雍容大雅),最合于主席的气魄、风度。
《毛选》英译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开始参加英文翻译的有金岳霖、钱钟书、郑儒箴、王佐良等人,还有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爱德勒等一批外国专家,一年以后,只剩下钱锺书和几位年轻助手。钱锺书平时就住在城里,一般周末才回校住,并继续指导他门下的研究生。《毛选》英译委员会的主任是1924年毕业于清华的徐永煐,他非常欣赏钱锺书,笑称钱是自己的“officewife”(办公室伴侣)。两人共事最久,由于合作愉快,后来由上下级成为要好的朋友。
从1950年7月至1954年2月,钱锺书一直从事《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工作,“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这项工作正如他自己说的——“并不是那么好做的”。《毛选》的英文翻译与中文原文的编辑在同步进行,原文在编定过程中不断修改,英译也不得不跟着变动,往往是一篇已经定下来的译稿反复地改个不停。另外,也存在认识不一致的情况,杨绛说:“好在锺书最顺从,否了就改,他从无主见,完全被动,只好比作一架工具。不过,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锺书在工作中总是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钱锺书做事认真,办事效率却不低,别人干一天的活他半天就能干完,甚至两个小时就干完;省下来的时间就偷空看书。他甚至认为《毛选》英译委员会的最大好处是“人少、会少”,搞运动也声势不大,有时间读书。
在这期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钱锺书虽还在城内,但已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文研所的编制、工资属新北大,工作则由中宣部直接领导(1956年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4年2月,翻译《毛选》工作告一段落,钱锺书回到文研所工作。1957年“反右”时,在所内的“拔白旗”运动中,除《宋诗选注》受到“缺席”批判外,他本人并没有被打成右派。1960年夏,《毛选》第四卷英译工作开始,1961年春完成。钱锺书没有参加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但做过“润色”。
《毛选》的英译分为翻译和定稿两个阶段。1958年初到1963年,钱锺书成为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据说,这是胡乔木推荐的。徐永煐写于1962年3月的《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对前三卷“英译旧改稿”的修改工作,“建议由程镇球、SOL(即SolAdler,中文名爱德勒)、钱锺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专责整理历次修改建议”;在介绍钱锺书时,他写道:“(钱)汉文英文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文学研究所现在让他每星期在翻译组工作两天。他只能参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为陷于会议,更不能发挥全面和深思熟虑的作用。如果把这三人摆到一起,担任全面、细致的衡量性的工作,则能收政治和技术、英文和汉文、旧人和新人结合的效果。”钱锺书大概是作为“技术”、“旧人”的一方被“结合”进去的,至于“英文汉文”兼擅于一身,比之程、SOL两位似更具优势,而“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则是无人可比了。可见他在整个《毛选》翻译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选集〉英译内情点滴》,《悦读》2007年11月)
翻译毛泽东诗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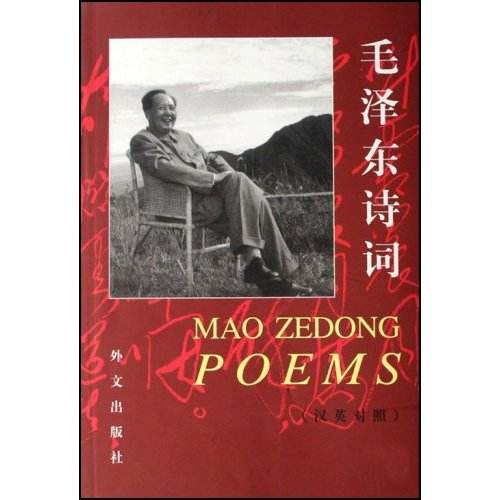
1963年英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结束,1964年,钱锺书又成为“翻译毛泽东诗词五人小组”成员,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已经翻译的全部毛泽东诗词,最后出单行本。
这“五人”的另外四人是袁水拍、乔冠华、叶君健和赵朴初。袁水拍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诗刊》杂志编委,叶君健是英法文版《中国文学》主编。在“五人小组”成立前,外文出版社已出版了由安德鲁?博伊德等译的《毛主席诗词》英译本,但译文并不令人满意,袁水拍还特别撰文批评。叶君健是《毛主席诗词》英译本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他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成立一个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锺书、叶君健作为成员。钱锺书与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袁水拍与乔冠华主要负责对原作的解释和对译文的斟酌。有关部门同意了这项建议。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新发表的诗作,后来小组又增加了诗、词、曲名家赵朴初作为成员,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工作地点在中宣部三楼会议室。
翻译期间,乔冠华经常用他的汽车送钱锺书回家,也常到他家坐坐,说说闲话。叶君健曾回忆钱钟书在“五人小组”中发挥的作用:“所幸我们小组中有赵朴初那样著名的诗人和钱锺书那样有修养的诗评家,这样,我们最后译文的‘风格’,还基本上能达到一致认可的程度。”(《文汇报》2008年5月6日)
“文革”开始后,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工作暂时停止,钱锺书此时才真正尝到运动之苦。1966年8月,他被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5月,革命青年夫妇搬进他们家合住,不久,钱锺书被下放干校。1972年3月从干校回来后,他与合住者发生争执,被迫“逃离”原房子而暂住北师大,大病一场,差点送命。最后,他迁入学部七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后期工作就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1974年11月,江青要求“五人小组”继续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也有文章说,是周恩来调钱锺书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怕他被下放干校折磨而死。翻译期间,由于钱锺书年初才大病,他要求“足不出户”。翻译小组成员不得不每天来陋室工作。“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幸好所有的人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我们仨》)袁水拍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换个大点的房子,江青也同意他们搬到钓鱼台工作,但钱锺书不愿意。
1976年“五一”节,《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本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个英译本,后来成了接着出版的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
“革命者”不敢对钱锺书“太革命”
1949年后,钱锺书从担任《毛选》翻译工作开始,就一直从事和政治关系密切的译事,他本人因此确实受到了一些积极影响和不一般的待遇。1957年的反右风潮中,钱锺书在1956年“黑材料”的风波下,居然有惊无险,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
钱锺书政治地位的抬升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上调”翻译《毛选》一开始,他的政治地位就显然比同类知识分子要高。这一“上调”固然是因为他精湛的外文水平令高层不能不格外重视与重用,无形中也大大提高了钱锺书作为技术专家的业务地位。柳鸣九就说道:“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语言业务上对钱钟书的重用,首先就表明了政治上的信任,而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长期任职,而且在定稿工作中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也证明了他尽心尽职,为政治服务的良好态度,以及他这种服务的优质优量,这就使得他完全成为了共和国真正的一级专家,成为党与政府所重视的‘国宝’。”(《“翰林院”内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不仅使钱锺书避过了风头,还享受到了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无法享受的待遇。1958年知识分子下乡改造,钱锺书于12月初下放昌黎,到次年的1月底就回来。从1958年初到1963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此时“三年饥荒”已开始,钱锺书回来后,因1959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5月他们家也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但并不担心吃饭问题,一家人常出去“逛市场”、“吃馆子”。杨绛说,因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的有外国人,他们还“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我们仨》)上世纪50年代,钱锺书每年都会收到“五一”、国庆观礼的邀请。1962年8月14日,他们又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阳台,他们新添了家具,住得很“宽舒”。有回忆说,翻译《毛选》期间,吉林通化市给毛泽东送来一批葡萄酒,中宣部给了每位干部一瓶好酒,钱锺书也得到一瓶。
“文革”中钱锺书虽也遭到不幸,但万幸的是没有被抄家,还可以继续写日记,做笔记,并完整保存下来。“文革”结束初始,他就拿出了皇皇巨著《管锥编》,这是其他知识分子做不到的。故有学者总结道:“因为他曾翻译《毛选》和《毛泽东诗词》,‘革命者’念其‘革命’贡献不敢对他太‘革命’。”
钱锺书是“御用翻译”吗
1998年12月,钱锺书去世。他在1949年后所做的这些翻译工作,被官方再次提及并放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的李铁映在《人民日报》撰文怀念钱锺书:
自五十年代以来,钱锺书出色完成了党和国家委托的工作。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锺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深切缅怀学术文化大师钱钟书》,《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6日)
“文革”结束,钱锺书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还连任了几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也都说明官方对他这位非党学者的另眼相待。那么,钱锺书是否真如有些人评价的,是“御用翻译”呢?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称呼并不恰当。
其实,这些翻译工作只是集体工作,是政治任务,并非他的本职工作。如果说钱锺书翻译《毛选》与毛泽东诗词“是最重要的学术活动”,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是存在偏差的。杨绛一再强调,“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徐永煐的传记中就说:“毛选英译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凝聚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翻译家的智慧和心血。”在英译毛选小组中,钱锺书一直是以英语专家的身份被肯定的。杨绛也说:“钱锺书从未把翻译毛选和以上这类任务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他自己填写的个人履历中,从未写入以上经历。”“都是有关部门向钟书所在单位借调的”。没有当成本职工作是真,但钱锺书在填写履历时,并不回避这段经历。如1955年,钱在填写中国作协会员表时,在“近三年来有何新作”栏写道:“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现在尚部分从事此项工作),故无暇顾及其他活动。”
像钱锺书这样在简历中写译《毛选》的事,在以后几乎没再见到。他并不希望自己因此而被记住,而是尽量淡化此事,更不要说以此为炫耀的资本,向组织提要求。这一点和解放后郭沫若、冯友兰等人的表现有巨大差别。翻译毛泽东诗词期间,很多人写“鉴赏”类文章,连毛泽东自己都认为“注家蜂起,全是好心”。有钱锺书的传记作者称,钱锺书是很有条件写的人,但在阿谀奉承之风盛行之时,钱锺书一反时流,不著时文,不发时论,仍默守学术独立的立场。“文革”后,钱锺书对这些经历更有意轻描淡写。1979年,他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余英时向他求证是否如外界所说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钟书说,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委员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自己没有做过毛的秘书,也没译过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余英时道:“他说不是那么回事,他翻译《毛选》也没做什么事,只是别人翻译的,他来看看。”“他只校阅,未参与译事,翻译的另有其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一般性专业人才极其缺乏,大学者从事与国家有关的诸如翻译这类事,其实是很正常的。那时,参加《毛选》《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等各语种翻译的专家学者难以计数(《毛选》前三卷约有30多种语种的翻译版本),钱钟书也只是其中之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从事这类工作是非常荣耀的,有些专家学者还积极主动要求参加,如翻译《毛选》第五卷时,年过六旬的北京大学著名英语教授李赋宁是工作开始后又自己主动申请来参加的。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钱锺书再次被抽调到中共八大翻译处担任外事翻译。这次调来的还有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专家,有杨周翰、李赋宁、吴兴华、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吴景荣等人,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教授也在其中。翻译处设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大旅社,钱锺书住在北大,每天搭公交车上下班。后来工作紧张,他们就都在那儿过夜了。参与翻译的巫宁坤回忆:“我们的工作繁重,翻来覆去翻译一稿又一稿的政治报告,还有数以百计的代表发言,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错误’。有时我们还加夜班。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英、美的著名学府或国内的教会大学毕业的,都心甘情愿为共产党的会议效劳,这足以显示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成功。同时,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训。”(《一滴泪》)国庆前大会闭幕,钱钟书和王佐良、巫宁坤奉命留下来,对全部会议文件的英文译文再次加工定稿,三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一周工作6天,直到11月中旬。
从巫宁坤的回忆可以看出,中共八大时大批教授做外事翻译,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是心甘情愿的。巫宁坤在八大之后的国庆游行中,被邀请到观礼台,学院为他有幸参加国庆观礼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甚至感到羡慕。曾参加过《毛选》翻译的人回忆说:“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当时如果能参加《毛选》翻译工作,自己会认为是莫大的荣誉,而别人则会投以羡慕的目光,所以这些同志都是带着一种深深的自豪感在兢兢业业地、一丝不苟地投入工作,无一懈怠者,而且环境气氛也不容许有任何懈怠者。”
确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人敢懈怠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正当盛年的钱锺书难以说“不”。钱锺书在解放后非常“识时务”,少说话,多做事,在得到信任做翻译工作期间,更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据许渊冲回忆,钱锺书在英译《毛选》工作中,和金岳霖他们比起来,也不怎么显得出众,平时很谦虚。1953年,翻译《毛选》期间,友人郑朝宗到其工作处看望他,他出示了一首新作,其中有一联云:“疲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焦急不安的心情跃然纸上。(《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钟书在一起》)巫宁坤回忆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有一天,他看到一篇国家领导人的发言,觉得文字累赘,很难译成像样的英文,随口大声说:“你拿这种呆板的文章怎么办呢?”钱锺书马上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巫说:“当时双百方针甚嚣尘上,我没想到以语多锋利闻名的钱先生竟会如此谨小慎微,心里很不以为然。不过一年多以后,我就以言获罪,从此和钱先生一别二十余年。深夜扪心,想当年少不更事,自作自受,辜负了钱先生对我爱护的一番情意。”
在1949年后所有的这些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要数最先翻译的《毛选》了。那么,钱钟书对此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从现有的回忆文字看,他对这项工作还是非常认真的,但他的内心却另有一番想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政治分类。报告中提到当时北大的一部分“反动教授”,特别点到了钱锺书,说他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钱钟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这份报告还称钱锺书在解放前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这份报告,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别人贴钱锺书的大字报时他才得知。钱在大字报旁贴出了申辩的小字报,说自己一向敬仰毛主席,正因如此,他才认真负责地主持审定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对毛主席著作有丝毫不敬之处。举报的内容虽查无实据,但当时军宣队认为“告发”的事情情节严重,料必事出有因,还是命钱钟书写了一份自我检讨。杨绛晚年对这份报告一再进行了反驳和否认。这份报告中关于钱锺书的言论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中央后来没有核实清楚的话,他在1957年是无论如何逃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的。但,钱钟书如果没有这个意思,难道是空穴来风?
这种大学者、专家从事一般性翻译工作的情况,直到“文革”后才慢慢改由专门机构来负责。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与领导人著作翻译并行的另一大项是中译外工作,即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文件翻译。将党代会的文件译成外文,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期就开始了;1969年的九大和1973年十大的文件,也由外交部和新华社牵头从各单位调人集中到人民大会堂译出;十一大召开时正值翻译《毛选》第五卷,所以它的文件是由这个班子完成的。此后,从1978年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始,以后的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的文件就都转由中央编译局文献部负责组织。1985年以前,会议的翻译工作都是在饭店或招待所完成的;自1985年始,为了节省开支,又同样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这项工作便由中央编译局承包了。
余英时说钱锺书“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以此话为底线,我们就不该太苛求于钱锺书。在一个政治和社会生活极不正常的年代里,对更多的诸如钱锺书一类的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报之以同情的理解,他们的损失与伤痛并不比其他人少。
如果一定要给钱锺书1949年后从事翻译工作的这段经历下个论断的话,那只能说:奉命而已,仅此而已。
(作者:钱俊之,文史学者)
